新用户登录后自动创建账号
登录香港书展的文化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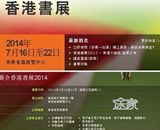
香港人每年只买一次书,而且是在香港书展期间购买。虽说有点夸张,但也说明香港书展很受老百姓关注。2013年的香港书展有98万人次参与,人均购书790元港币,书展为参展商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言而喻;然而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文化价值却比经济效益更为影响深远。
二十多年来,书展培养了香港人通过书展感受文化的习惯,图书零售也不再是书展的唯一内容。书展推出的文化活动吸引了更多市民参展,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零售,让书展在文化与商业间良性循环。
早年的书展定位
早在香港书展开办之前,香港的出版商会每年都自行举办小型书展,由于规模太小,所以影响力有限。出版界一直希望能够把书展办成规模更大,更专业,更能服务业界的平台。
于是,官方授权成立的非政府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接过了这一使命,于1990年开启了首届香港书展。从1990年到2013年,香港书展走过了24个春秋,在华语文化圈的认知度逐年提升。
前几届书展的定位更多是为参展商服务,也就是为出版界提供一个专业化的图书零售平台。参展的图书中,漫画类、儿童类产品占据了重要份额,因为这类书的市场表现比较好。
1993年,抢购精品漫画的市民过于拥挤,将售票处旁的玻璃挤碎,致使两名入场人士受轻伤入院,给第四届香港书展蒙上阴影。该事件引发了关于书展定位的思考,由于行业内没有统一的意见,所以后续书展的基本理念依然没有改变。
1997年的第八届香港书展增设“国际版权交易会”和“亚洲出版研讨会”,推广版权贸易。从香港书展增设版权贸易类项目可以看出,这时的香港书展依然将出版商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到1997年,香港书展已经举办了八届,但民众的参与度并不高。民众参与度低又客观上影响了图书零售等商业活动,也客观上影响了贸发局的收益,让贸发局面临经济压迫感,毕竟书展费用并非来自政府支持。寻找一种既能提高民众参与度,又能实现书展文化使命的模式是大势所趋。
文化与商业复合依存
1998年,香港贸发局决定倾听民间的声音,做了民意调查,最终将漫画类展品移出展馆,只允许展出和出售第一类书刊。这一决定让书展成为适合民众全家参观的活动。虽然这一行为让漫画界的出版人表示不满,但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随着民众参与的提升,贸发局的服务理念慢慢向参展观众倾斜,比如,增设“大学访”,提供书籍速递服务,开设全套的餐饮休闲服务,进一步完善服务参展民众的体系。通过服务观众间接帮助参展商获得经济效益成为书展的新理念。
香港贸发局很快发现了服务民众带来的经济效益。随着参展人员增加,参展商的收益也有明显增长,贸发局通过门票收入也减少了经济压力。于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参展的民众,香港贸发局于2001年决定邀请艺术发展局协办书展并与各种文教机构联手推出一系列文化活动,将书展办成暑期香港文化阅读周。
这届书展的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基本模式为后续书展所沿用。此后的几届书展,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民众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参展商的经济收益也越来越好。
经过一番探索之后,建立在商业上的文化活动成为香港书展主推的项目。让文化活动吸引民众参与并消费,通过民众消费提高经济效益,即文化与商业的复合相互依存模式渐露雏形。
此后的书展中,香港贸发局基本能维持收支平衡或微赔的局面,让香港书展的商业模式逐步成熟起来。今年书展推出的名家讲座系列以及书展走进民间等活动,全都是这一书展理念下的产物。今年书展的活动质量与数量可谓历年书展之最,文化气息更为浓郁,文化格局也更为宽广。
让书展进入社群
用商业带动文化,再由文化推动商业的理念获得成功后,香港书展进而将展馆内的模式复制到香港的社区。文化与商业的复合相互依存在社区中一样取得了好的成绩。2007年,香港书展第一次走出展馆,举办了“阅读香港:地标之旅”和“阅读香港:书店之旅”两个活动。这些活动让文化人走出展馆,与读者一起阅读城市空间、文化历史,把阅读的乐趣从书展带入到社区。
书展活动进入社区后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拉动了读者的消费。展馆外的活动也慢慢与商业活动挂钩,在文化与商业上寻求平衡点。近几年的书展外展活动不断增加,支持与合作机构越来越多。书展进社区活动也从一开始的两场活动扩展到了一百多场。这些活动中只有部分是贸发局牵头组织的,更多是合作机构主办的。
2012年香港书展的“文化七月·悦读夏季”活动将书展延续到整个7月,在商场、书店以及文化机构组织了50多场活动,让文化人与读者近距离交流。这个活动系列取得了较大成功,为今年的香港书展活动提供了样板。无论从活动的数量与覆盖的区域还是民众参与度来看,2013年书展的成绩大于2014年,“文化七月”系列活动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岛性文化狂欢。
结语
想玩得有文化有品位,香港书展是很棒的选择。你不仅能看到嫩模表演,还能看到一线明星的秀场,同时也能见到打牌文化名人开坛讲课。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人一年只买一次书的原因。



1.jpg)




.jpg)






